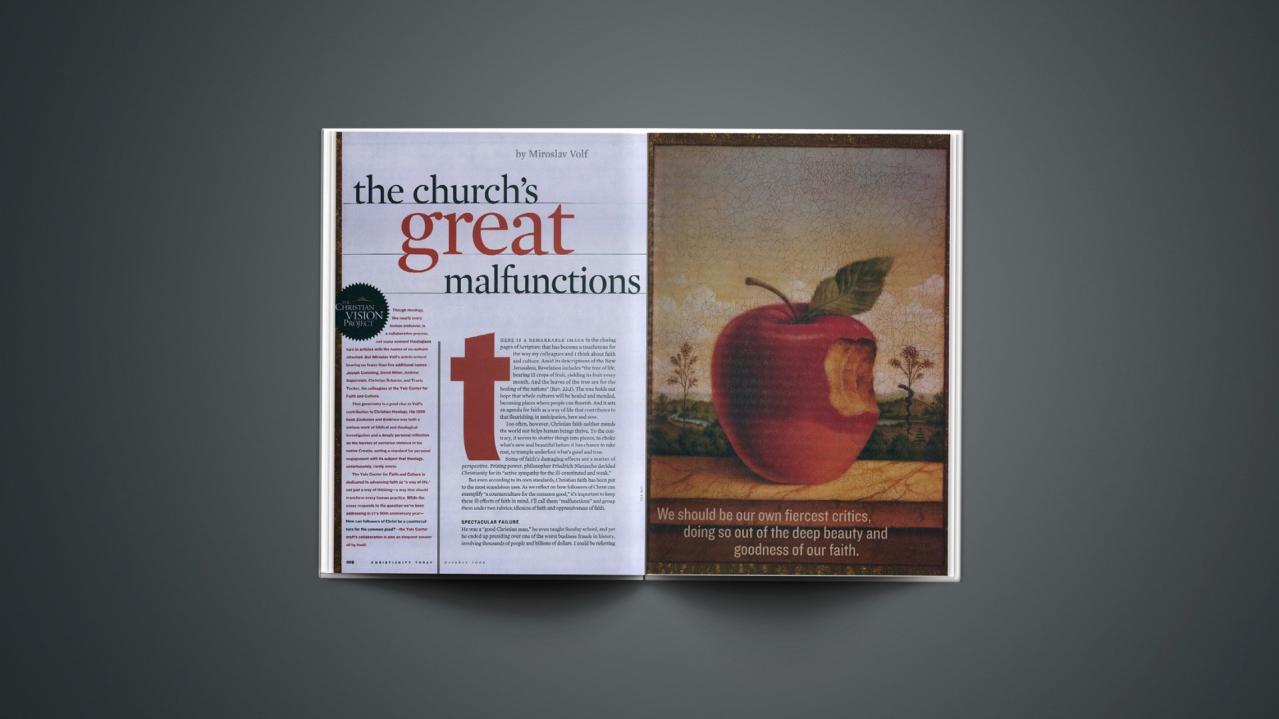| 今日教會的嚴重失能 |
| 我們應當成為自己最嚴厲的批評者,因為這樣的批判,出於我們對信仰最深刻的美與善的認識。 |
| (2025年07月31日) |
|
本新聞提供者: Christianity Today
(作者 沃弗 (Miroslav Volf))在聖經結尾的篇章中,有一幅極為動人的圖像,是我與同工們在思考信仰與文化關係時的重要參照點。那是一幅描繪新耶路撒冷的景象:「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,結十二樣果子,每月都結果子,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」(啟示錄22:2)。這棵樹指向一種盼望——整個文化都能被醫治與修復,成為人們生命能真正繁榮、茁壯的所在。而這幅畫面也為基督信仰作為一種「生活方式」定下方向:在此時此地,就以這種盼望為目標,積極地參與在其中、預嘗其果實。新耶路撒冷,是已然和未然。 然而許多時候,基督信仰既沒有修復這世界,也沒有幫助人類經歷真實繁盛的生命。相反地,信仰似乎反而將萬事撕裂、粉碎,在新生命與美麗的事物尚未扎根前就將其扼殺,甚至踐踏真理及美善。 當然,信仰所帶來的一些傷害性影響,有時只是不同觀點的問題。崇尚權力的哲學家尼采 (Friedrich Nietzsche) 便曾譏笑基督信仰那種對「體質孱弱及軟弱者的積極憐憫」。 但即便依照基督教自身的標準來看,基督信仰也曾被用於最令人震驚的用途上。當我們思索基督的跟隨者該如何活出「為了公眾益處而逆著主流文化 (counterculture) 而行」的見證時,我們也必須記得「失衡的信仰」所能造成的負面後果。我稱這種行為為「信仰的失能」(malfunctions),並歸納出兩大類型:怠惰的信仰(idleness of faith) 與強制的信仰 (oppressiveness of faith)。 惡名昭彰的失敗有這樣一個人,曾是位「好基督徒」,甚至擔任主日學老師,然而最後卻主導了歷史上最嚴重的商業詐騙案之一,牽涉上千人、金額高達數十億美元。而這號人物可以是這些年來新聞商業版頭條上的任何一位高層主管,從安隆 (Enron) 到世通 (WorldCom),乃至其他案例。為什麼他們的信仰無法阻止他們犯下這些罪行?我猜,至少有三個因素導致他們的信仰如此慘烈的失敗。 第一,誘惑的吸引力。某種程度上,商業詐欺與婚姻中的不忠或學術寫作中的抄襲並無不同。即便是奉行高道德標準的人,也可能屈服。 人類屈服於誘惑的軟弱幾乎與人類歷史一樣悠久,但戰勝誘惑的歷史也是。擁有好的品格比擁有「道德知識」更為關鍵。就像《創世記》裡墮落的亞當與夏娃,或《羅馬書》第七章中自白的使徒保羅一樣,多數行惡的人其實知道什麼是對的,只是無法抗拒罪惡的吸引力。當人的品格枯萎,信仰便陷入怠惰。 第二,體制的力量。誘惑的吸引力會被我們所處的體制放大。這一點,在幾乎無所不在的市場體系中尤為真實,無論是思想市場、商品與服務市場、政治影響力市場,或是大眾傳播的市場。早在一個多世紀前,社會學家馬克斯·韋伯 (Max Weber) 就形容現代市場為一座「鐵籠」。市場的遊戲規則要求利潤最大化;是這些規則——而非道德考量,決定了遊戲該怎麼玩。而必須在這些各自運行著內部邏輯的領域中生活的基督徒,難免會過著分裂的生活。 現代社會中多數擁有信仰的人,都曾經歷過「忠誠度分裂」的拉扯。雖然許多人選擇了妥協,但也有許多人堅持信念,當體制的規則與他們內心深處的信仰價值相衝突時,他們拒絕照著遊戲規則行事。他們明白,自己必須在各個層面上都活出信仰——不僅在靈魂深處的內室中、在私人生活裡,或在教會與志同道合者聚集的時候,更是在每日奔波於各個生活場域、從事日常工作時——見證自己是有信仰的人。 第三,對信仰的誤解與扭曲。卡爾·馬克思 (Karl Marx) 有句著名的評論,說宗教(尤其是基督信仰) 是「人民的鴉片」,是一種令人沉迷的鎮靜劑,使人與現實隔絕,靠著對天堂的幻想來安慰人心。但馬克思忽略了一點:宗教有時其實也像「興奮劑」,激勵人們去完成手邊的工作。然而,事實是,當基督信仰只被用作安慰劑或提升表現的興奮劑時,這樣的信仰其實已經「失能」了。 誠然,基督信仰確實承載著兩大傳統,大致對應信仰的兩種功能:「拯救」與「祝福」。作為一種拯救,基督信仰修補破碎的身心靈,包括醫治我們所承受的傷痕與苦痛;作為一種祝福,基督信仰賦予我們力量,使我們能以必要的能力、專注力及創造力,卓越地完成使命。 然而,如果基督信仰的功能「僅止於」醫治與賦能,那它就只是一根拐杖,而非一種生活的方式。確實,有些宗教的確就是如此——例如各種神祕主義信仰,包括新時代靈性運動 (New Age spiritualities)。但基督信仰並非僅此而已。真正的信仰之工,是引領我們踏上一段旅程,在旅途中引導我們,為我們所行的每一步賦予意義。 當我們擁抱信仰 (更準確地說,當上帝主動擁抱我們),我們就成為新造的人;我們的品格應被祂塑造、也被呼召成為耶穌王國的一分子;我們被邀請進入那關於上帝介入人類歷史的大故事中。當我們踏上這段旅程時,信仰為我們指出當走的正道與應避開的黑暗小徑。 最終,信仰的敘事賦予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意義,無論是最微小的舉動,或是最重大的決策。如果我們所做的事與這個大故事一致,那它就是有意義的,並將長存至永恆,如同不會被腐蝕的黃金閃耀發光;但若我們所行的與這個大故事相悖,那它終將失去意義,即使當下那是我們所做過最興奮、最有成就感的事——也終必如野草般燒盡。 若要使基督信仰在這世界上不變得怠惰,醫生與清潔工、企業主管與藝術家、全職父母與科學家的工作,都必須被納入上帝與這世界的大故事中。上帝的大故事應該成為所有在這些領域的人玩遊戲的根本原則;並且這個故事,應當塑造參與其中之人的品格。只是我擔心,今天無論在商業領域或其他任何領域,真正以這種方式思考自己信仰的人,實在少之又少。 暴力的信仰對基督徒而言,信仰是一份珍貴的禮物,是個人與社會最有價值的資源。當這個信仰未被善用時,受損的不只是基督徒才有的益處,更是整體的公共福祉 (Common Good)。然而,對今日許多非基督徒而言,基督徒在信仰上的「怠惰」反倒成了他們的「小確幸」;因為他們真正懼怕的,是「積極的信仰」。正如哈里斯 (Sam Harris) 在《信仰的終結》(The End of Faith) 一書中所說,《聖經》充斥著「毀滅生命的胡言亂語」,而當基督徒將《聖經》視為最高權威時,他們就會以暴力、壓迫、強制、毀滅生命的方式行事,從而危害公共利益。 一名塞爾維亞士兵站在坦克上,得意洋洋地比出三根手指——象徵至聖三一的記號,代表自己隸屬一個「正確地認識上帝」的群體。顯然,他的信仰在某種意義上,賦予他在這台殺人工具上凱旋前行的正當性。他並不孤單;許多像他一樣的人,將嗜血的戰神或狂熱的民族主義女神,披上宗教信仰的外袍,使之合法化。他的一些克羅埃西亞敵人也是如此;而許多美國人也同樣熱切地將十字架與美國國旗合而為一。他們跟隨歷史上許多基督徒的腳步,走在一條充滿鮮血和眼淚的路上。 因此,批評者認為,當基督教或其他主流宗教宣稱這世界處在「善與惡的終極之爭」時,註定會導致暴力。然而,若宗教對邪惡之事完全不加抵抗,所帶來的暴力結果可能比善惡之爭還更嚴重;況且,並非所有的善惡之爭都等同於暴力。 批評者控訴,一神信仰尤其容易將世界劃分為「我們」(真神的信徒) 與「他們」(拜假神的人)。但實際上,多神信仰在本質上更容易分裂人們,因為它讓人各自崇拜彼此相衝突的神明,所造成的「我們/他們」界線甚至比一神信仰還要徹底。並且,如果我們將關於「真理與否」的問題從宗教中移除,那麼在多神對立下,要裁決哪位神明更值得膜拜的唯一方式,就只剩下暴力爭戰。而無神論也並未遏止史達林、毛澤東與波爾布特 (Pol Pot) 的屠殺暴行。 當然,基督教本身並不只是單純的「一神信仰」。基督信仰對上帝的本質與人類歷史所提出的獨特主張,是真能使人類生命繁榮的有力資源。批評者視基督之死為「上帝的虐兒行為」,但基督徒所相信的,是耶穌並非與上帝分離的「另一位」,而是上帝本身的「另一位格」。在十字架上,上帝親自將人類犯罪的後果承擔在祂自己身上。新約聖經堅定地主張,這種神聖的行動成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榜樣、目標:人不應試圖主宰與征服,而應自我犧牲與憐憫。 批評者指控《啟示錄》的異象描繪了一位神聖騎士屠殺所有與上帝為敵的人,但《啟示錄》從未鼓勵基督徒模仿這位騎士;事實上,聖經要求基督徒去效法那些為信仰犧牲的殉道者,效法暴力的受害者。那些持續拒絕被那「自我犧牲的愛」所拯救的暴力之人,難道最終不該被隔離在充滿愛的世界外嗎?騎著白馬的神聖騎士的「暴力」,不過是神聖地實現最終的審判所帶來的永恆隔離。 那麼,為何有些明明信奉和平之道的基督徒,卻常在言語或行為上如此暴力呢? 我認爲主要有三個原因,大致對應讓信仰怠惰或失能的三個理由: 1. 信仰太過膚淺 太多基督徒雖然擁抱信仰對基督徒的要求 (例如維護未出生生命的神聖性,或追求公義的社會制度),卻忽略了基督信仰要求我們達成這些目標的「方式」:基督信仰要求我們說服人們、而不是強制/暴力要人接受。但對付因宗教導致的暴力 (包括言語上),解方並不是「越少人有宗教信仰更好」,而是「更多人應擁抱信仰」——更完整、更全面地實踐基督信仰;聖潔之人以勇氣及誠信活出的那種信仰;優秀的神學家們以負責任的態度深度反思的那種信仰。 2. 看似與生活毫無關聯的信仰 一個兩千多年前誕生的信仰,能否對今日的民主政治、企業管理或國家在防衛恐怖主義等議題上,提供任何有用見解?但常常當我們感受到這種張力時,就只是利用信仰來為我們原本就想做的事背書。 要在不斷變遷的時代中,真誠地理解並實踐信仰,是一種困難的智性與屬靈操練。這種努力不能只是神學家的責任;它必須成為每個基督徒共同參與的努力,也需要涉及多個學術與實務領域的對話和學習。 3. 不願走窄路 我們常把「不太容易實踐」的聖經教導歸結為「要求太高」。有人傷害了我們或我們的群體,我們就會產生報復的衝動——於是我們把「愛仇敵、善待仇敵」這個明確的基督命令拋諸腦後。又或者,我們認為整個文化正在走向毀滅的深淵,於是想力挽狂瀾,卻忘了基督信仰的嚴格標準:無論目標多珍貴、多正確,都不能以錯誤的、不合宜的方式達成。 因此,我們最終又回到「品格」這個核心問題。除了要將「被正確地認識」的基督信仰應用於生活各個領域,我們還需要那些靈命被良好塑造的人,能夠抵擋把信仰用在壓迫、強制他人的誘惑。因為當基督信仰淪為一種僅供個人或文化利用的資源,而不是引導人生命樣式的聖潔力量時 (例如那位塞爾維亞士兵),信仰所導致的後果會是毀滅性的。 前方的使命那麼,基督信仰真的還有可能在經歷這兩大令人不安的「失能」(怠惰及強制) 後,恢復其應有的樣貌嗎?答案是:唯有當我們以誠實揭露這些失能,深知我們的救恩並不取決於我們在道德上的完美時,才有可能。身為基督徒,正是出於我們對基督信仰最深刻的美與良善的認識,我們應當成為自己最嚴謹的批評者。 唯有如此,我們才能重新思考基督信仰的本質:基督信仰不只是關於「應當相信什麼」的一套命題系統,也不僅僅是一種能帶來安慰或激勵的技術及操練,而是一種整全的「活在世上的方式」(an integral way of life)。這種信仰實踐,不會是一種與真實信仰群體脫節、大放厥詞的外太空「公共神學」;相反的,基督徒對公共福祉的追求,必須根基於教會,卻「不以教會為中心」。 我們需要建立並強化這樣一種成熟的信仰群體:既有願景也有品格——當基督徒一同聚集敬拜上帝時,他們的信仰成了一種生活方式,並在被上帝差派後,分散於世界各地、各行各業,將這信仰活在他們每天肩負的各種職責與使命中。 在這一切過程中,我們若能同時從非基督徒的付出中學習,將大有助益。任何自視為「逆文化而行」(counterculture) 的群體,都容易陷入一種試探:以為自己與社會/圈外人的關係是種「對立關係」。但對於相信上帝是萬有真理、良善及美的源頭的人而言,這種全面性的否定並不正確。我們不需要把「埃及人的金子」全部熔掉。有些非基督徒的觀點或方法可能確實需要拒絕,但也有一些可以原封不動地接納,還有一些則可以修補、改進後加以應用。 身為一個逆文化而行的群體,基督信仰之所以參與社會、尋求社會的公共福祉(common good),是因為我們相信那位獨一真神給予眾人普遍恩典 (common grace),而我們願為天父世界的共同益處而努力。 (本文原發表於本刊2006年十月號) 耶魯大學「信仰與文化中心」致力於推動基督信仰成為一種「生活方式」,而不只是某種「思考方式」——這種信仰方式應當能轉化人類的各樣實踐。本文回應了本刊於創刊50週年時提出的核心問題:基督的跟隨者如何能成為「為著公眾益處逆文化而行」的群體? 沃弗 (Miroslav Volf) 為克羅埃西亞裔的福音派神學家,現任耶魯大學神學教授,創立耶魯信仰與文化中心 (Center for Faith and Culture)。他以研究和解、公共神學、全球化與基督徒身份著稱,代表作包括《擁抱神學》(Exclusion and Embrace)、《公共的信仰:基督徒社會參與的第一課》(Public Faith: How Followers of Christ Should Serve the Common Good)。 |
| 新聞照片:
|
台灣聖經網 www.TaiwanBible.com